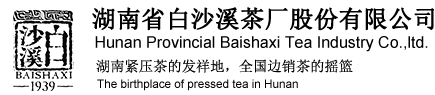26
2020/05
分享
熬茶,一种穿透政治的平民信仰仪式
发布时间:
2020-05-26 14:58
来源:
凌晨四点半,天降六月雪,沿山道至大经堂,右侧大茶房屋顶早已燃起了熬茶的炊烟。
大茶房始建于清康熙28年,内有五口生铜大锅,其中最大的一口直径达2.6米,深1.3米。大殿正中放置着3口铜锅,右侧分别挨着墙角一边一口。平日寺里早课集体诵经时只需要一口锅熬茶就够了。茶房角落里茶叶整整齐齐堆放着,有雅安藏茶,有益阳茯茶,还有湖南安化白沙溪茶厂的贡生尖。

熬茶
这些茶,都是四方信众的布施,信众喜好不一,财力不等,当这些茶进了寺院的茶房,就再也没有世人眼中那种高低等级的分别了。成规模的寺院,一般有专门的司茶喇嘛,熬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毕竟那面对的是信众的布施,所以不敢怠慢。
茶,在藏区的大规模流行有学者将其归因于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表面上看不过是一支和亲的队伍,但集结百业工匠逾5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从长安出发,那更像是一次带有援助性质的长途跋涉。唐朝与吐蕃建立的这种往来关系更多的是停留于政权的上层之间,文成公主进藏,确实从生活的很多方面影响了雪域高原上的民众。但唐宋时期,茶叶在西北及雪域高原依然还属于社会中上层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真正走向民众化的普及,还是在元朝时期。

民国时期塔尔寺的佛寺活动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一个统一多民族政权,作为封建王朝,其版图首次超越了汉唐。这一时期,雪域高原也正式纳入了中央版图。去年在甘肃武威白塔寺,第一次深度接触“凉州会盟”的内容时,我佩服萨加班智达的智慧,面对阔端背后强悍的武力威慑,选择了面对现实。从形式上讲,他给雪域写了个函,宣告并入了元帝国。从深远的意义上来看,至此蒙古人也开始皈依了藏传佛教。
在见阔端的时候,萨加班智达还带了自己才十岁的侄儿,在政治家眼里,这是一种质子之举,以此表达诚意。但没想到的是,后来那个“质子”继承了萨加班智达的衣钵,并且成为忽必烈的老师,引导忽必烈皈依佛教。他创立了元朝的官方书写文字,他的名字叫八思巴。13世纪,在大一统的元帝国基础上,他实施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传教。其后,经过了近三百年的发展,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日渐兴盛起来了。
于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信众组织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布施活动。其中,卫拉特蒙古活动尤为频繁,规模也十分浩大。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他们赶着牲口,带着金银、绸缎以及茶叶长途跋涉而来。到了17世纪前期,草原上的贵族王爷为了表示自己对信仰的虔诚,也开始亲自率队入藏布施。这些入藏的朝圣队伍,每次抵达目的地之后,完成了所有的宗教仪式,最后都得进行最重要的一项布施活动,那就是熬茶。
等清朝再一次完成了大一统之后,中央一直以来都在提防蒙古高原与雪域高原之间的串联。清廷对这种进藏熬茶学经的行为进行了约束,规定10人以上的队伍必须要经过驻藏大臣的批准。这个政策让蒙古草原上的信众开始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那种大规模的贵族熬茶活动被削弱了,但是让民间的自由信仰更加活跃了。雪域高原的寺院茶事,由贵族及上层僧侣开始朝着民众化的道路发展。

施茶
加拿大有一位中国中古宗教史学家James A.Benn教授写过一本专著,专门讲茶与中国的宗教文化史。很显然,James A.Benn教授的专著里主要叙述的还是中国汉族区的茶与宗教,忽略了草原和雪域高原上茶与宗教的具体细节。五世班禅觐见乾隆的时候,在茶上活生生的演绎了一场封建君王与宗教仪式发生矛盾时的微妙大戏。
班禅觐见乾隆,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给他赐茶,此时班禅扮演的是一个藩王的角色,接受皇帝的赏赐。紧接着,他们又移步须弥福寿之庙熬茶,在这个时候,班禅要扮演乾隆宗教导师的角色。但是乾隆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就选定一位阿哥代替自己去熬茶布施。他自己在整个仪式当中就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这一套流程的设计,是大清礼部与理藩院一同琢磨出来的,既不损害皇权,又不伤及宗教情感。我去年在《安化黑茶:一部在水与火之间沸腾的中国故事》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又两百多年过去了,熬茶的仪式依然在很多成规模的寺院完整的保留着。
接近清晨五点半,熬茶的喇嘛开始频繁的搅动大铜锅,铜锅里茶与奶已经融在一起沸腾了很久了。之后,他开始用一个巨大的漏勺滤出茶叶渣。茶叶渣用一个大号的塑料桶装着,一勺一勺的滤着,待茶叶渣捞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桶也装满了。这只是日常里一个早课的茶叶消耗量,塔尔寺的喇嘛每天都会做早课,熬茶也是每天早课的一部分。
接近清晨六点正,在大经堂外的喇嘛开始集体移步到大经堂内,不多时一群年轻的喇嘛从大经堂里走出来,径直走进大茶房,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奶茶桶,一桶一桶的端着走进大殿。大殿里的喇嘛们掏出随身携带的茶碗,从大殿里面由内到外,一排一排的给每个人都满上。这是他们的早餐,也是修行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仪式,让喇嘛们给捐赠茶叶的信众结成福田与施主的关系。一碗茶汤,连接僧俗,沟通天地。
下一页
下一页